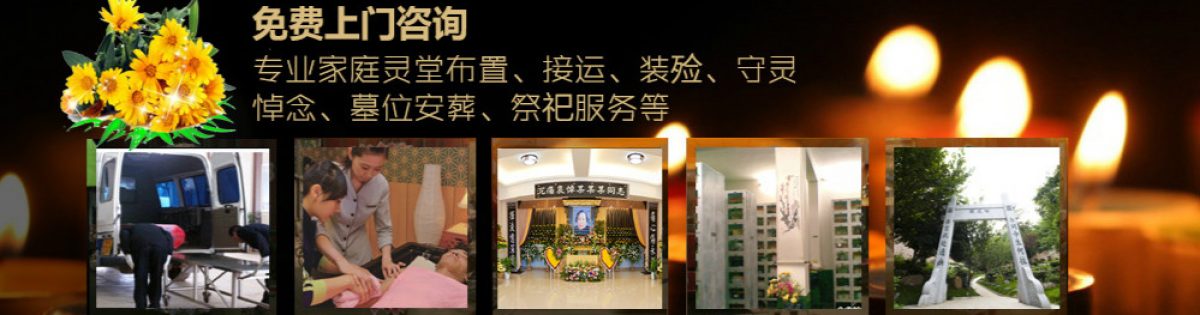古之服丧,均依礼制,亦因贫富有别而繁简不同。随着社会的发展,丧俗多有变化,有的与其他地区大同小异,有的却还保留着韩城古老的传统色彩和地方特色。
1、丧服丧饰
(1)、麻衣
麻衣以粗麻布制做,形如马夹,套于外衣之上。古时丧服以血缘亲疏分五等,为斩衰、齐衰、大功、小功、缌麻,统称五服。其服均以麻布制成,并按服的等级选用不同质地的麻布,且做工也有别,人称披麻戴孝便指此。目前,其他各服的麻衣均已消失,唯斩衰服(子、女的丧服)麻衣还在穿用。
除麻衣外,死者子女孝服一律不缝边,鞋也要象穿拖鞋一样趿着,以示哀痛而不饰边幅。
(2)、麻冠
以一寸多宽的麻布外裹以白麻纸,制成头圈状,两边各缀籽棉一朵,其上面前后方向缝同样质料的麻布条,成半圆状亦缀以籽棉,乡人称其为“系头子”,唯死者的儿子头戴此饰。观其形状,析其名称,当为古时孝子的束发之物,并非“冠”。大约是明代之后,才将“系头”改制,套于头孝之外,成为类似孝帽的饰物。
(3)、头巾
以麻布制做,宽尺许,形如古代皂巾,女子送葬、悠道时戴于头,故称“头巾”。平方顶,上缀籽棉,前有一尺多长的麻布片可以遮面,如面纱,后留三尺左右的麻布片遮至臀部。
(4)、孝杖
《礼纪·檀弓》记载,“居三年之丧(即斩衰,死者子、女服之),始死三日,水浆不入口,杖然后能行。”这说明孝子失去父母,悲哀至极,不思饭食,已到唯拄棍杖才能行走的地步。于是沿袭成俗,便有了孝杖。古时的孝杖以桐木制做,称“桐杖”,后人简而化之,以麻杆缠上白麻纸作为象征,唯死者子、女在送丧时执之,其他人不用。
2、丧仪
(1)、破孝
人死之后,主人便按服丧人与死者血缘关系的亲疏,给有关族人、亲戚扯送不同质料、不同尺寸的白布作为孝布,名曰“破孝”。
(2)、入殓
人一瞑目,立即洗理穿戴。就绪之后,即移尸于厅房。待尸凉,即入殓。棺木皆选松、柏板材,等级以块数愈少厚度愈厚愈好,最好者以四块独木做成,俗称“四片瓦”。在制作棺木时,一块板就叫“一条头”,由八块组成就叫“八条头”,十块就叫“十条头”,其他依次类推。底盖如由数块木板合成,必须均为单数,忌双数,以避“分尸”之忌。棺木形制通称“四齐”,略如平行四边形,朴实无华,稍有讲究者不过在两头各雕“寿”字而已。不象外地那样精雕细刻。据说,唯北京有此形制。同四合院一样,在棺木的制式上,韩城也受到北京的影响。
(3)、坐草
葬前,子女均要守灵。韩人守灵,须以干草铺地而坐,名曰“坐草”,为什么要坐“草”,乃远古穴居时代之遗风。
(4)、丘丧
人死入殓后,暂不埋葬,将棺木置于家中厅房,用砖裹泥封,数年或数月之后,再择日而葬,韩人称之为“丘丧”。丘丧之俗,古已有之,据现存北周宇文端墓志铭载,宇文端,北周元年(557)卒于任,武成元年(559)迁葬于乡里,从卒到葬,相隔两年。除此而外,在现有文字可查的历代出土的28方墓志铭中,丘丧时间最短者两个月,一年以下的8例,一至五年的14例,六至十年的3例,十七至三十三年的3例。何以久丘不葬,经济状况并非主要原因,因为墓主多属仕宦之家或书香门弟,夫死丘丧等妻死再行合葬,可算其中一个原因,但也只占了三例。其他拟或等儿子长大,或待事业有成,或其他原因,只能待后考究了。但丘丧为韩城昔日一种典型丧俗,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,直至建国后始绝迹。
(5)、铭旌
铭旌者,便是把颂扬死者的文字写在竖置的红色绸、缎上,送葬前,置于灵柩之旁,送葬时,打于灵柩之前,以为荣耀。铭旌,一般长一丈二尺,有闰月者加一尺,血缘稍远者,一丈或九尺即可。
(6)、选穴
死者入殓后,主人立即请人选穴挖墓。过去,多请风水先生看穴。建国后破除迷信,现多由主人自己选择墓址。但却大致遵循两个原则,一是方向,必须是头朝西北,足蹬东南。这大概与当地整个地理形势有关。二是两头不能空,即身后不能空,要头靠山丘或村庄,脚下不能空,足蹬山丘或村庄。墓道深度一般均在九尺以上,但必须掘至黄土层,取“哪里黄土不埋人”之意。
(7)、悠道
人死三天,凡嫁出的女儿均要返回婆家,一是给家里人报丧,二是回家准备葬礼。从娘家告别时,要从灵前哭至村外,边哭边诉说父母之恩和思念之情;从婆家来时,又同样从村外哭至灵前,韩人将这种沿巷哭诉称之为“悠道”。悠者,有吟、唱之意,因其声曼长而和谐,有悠扬之感,故称其“悠”。道者,道路、巷道也。在巷道中以悠扬的声调哭诉自己的悲痛之情,便是“悠道”一词的由来,古人在人死之后唱挽歌,而“悠道”也有一定的调式,且与秦腔中苦音慢板、滚白中的某些旋律有相似之处,可以说,“悠道”,便是古之挽歌的延续和存留。
(8)、暖窑
在送葬的前一天傍晚,孝子、亲戚都得到墓地去,在置放棺板的穴中四角点起灯,并在中间燃点麦草,有的则往四角各置燃红的木炭,乡人称之为“暖窑”。此举取“暖房”之意。人们认为,墓穴便是老人的“新房”,在老人住进之前,也要象人活着住新房时“暖房”一样(韩人把庆贺迁入新居谓之“暖房”)。这是孝子尽最后一次孝道的机会,当然,也是对筑墓工程作最后一次检查和验收,以便给第二天修整留有时间。
(9)、扯纤
古时送葬,拉运棺木用车,称“舆”,后来取掉了车轮,以人力抬送,但其形制仍保留了“舆”的名称,乡人称之为“丧舆”。在当年用车拉的时候,孝子扶灵车,族人晚辈(主要是男性侄、孙等)均在车前用绳子拉,似纤夫拉船,故称其绳为“纤”。后虽改拉为抬,但此俗尚存。出丧时,在丧舆上系数丈长的白布两条,上挽布圈若干,孝子扶丧舆,侄、孙等右肩套布圈,随抬丧舆者前行,乡人称之为“扯纤”。这里的“扯”,实为“拉”之意。
(10)、镇物
入殓时,在棺木中要放“四镇物”,即生铁、青石、木炭、朱砂。参照古之丧俗,这实际上都是一些保护措施的象征物,如置木炭,是为了防腐,置朱砂,是为了辟邪(直至目前,朱砂还是乡村应用最普遍的避邪物)。演变到后来,人们逐渐赋予这些物品以理想化的色彩。他们把生铁比为“东海长流水”,把木炭比作“南山福禄松”,把青石比为“西岭高山石”,把朱砂比为“北斗乾坤星”。其用意,就是给死人在阴间创造一个山高水长、福星高照的佳境,让其永享天年。至于在封墓穴之前,在穴中置放面灯、面鸡、竹弓、竹箭“四镇0物”,无疑是防盗措施的象征物。
(11)、打怕怕
有的地方称“作伴伴”。葬后当日傍晚,男孝子要去墓地再祭奠一次,并绕墓左右各转三周,口中还要念念有词:“左三匝,右三匝,你娃给你打怕怕,是神是鬼不怕它”。然后回家,至大门口,女孝子则“接怕怕”,哭至灵前即止。第二日仍旧,但只走到村外途中就返回;第三日更近,走到村口即返。如是者三日,即算完成了“打怕怕”的仪式,此俗源于古之“庐墓”,即孝子住在墓地为父母守墓。因古人对孝道特别重视,不管官居多高,只要是父母亡故,均得辞官回乡奔丧,并守孝三年,期满方能重新委任。在古时,确也有真正的孝子,真的住在墓地,三年不归家,《韩城县续志》记载“庐墓”三年者,例子不少。不过这毕竟是极少数,多数人尚做不到这一点,于是便象征性地以“打怕怕”的形式来表示不忍分离之情。
(12)、埋罐
古人埋葬,大都于墓中置放殉葬品,多为生活用具及食物。后人将其简化,于一小瓷罐中置米、面、筷子,封口,在埋葬之日,埋入墓道,意谓死人在阴间也能继续享用人间食物。翌日凌晨,孝子们便去墓地祭献,谓之“奠汤”,回来后过半个时辰,又去墓地祭献,谓之“埋罐”,实际“罐儿”已在先一天已经埋掉了,此行只不过是走个形式而已,其主要任务是男女孝子将孝杖插入墓冢两侧,男孝子并将所戴麻冠(系头)亦置于墓冢,宣告这两种丧饰丧具已完成其使命。随着丧仪愈来愈简,多数人已将“奠汤”及“埋罐”一次进行了。
(13)、期斋
乡人称人死后第七日为“头期”,葬仪一般都选在“头期”进行。以后每“七日”都要祭献一次,共过七个“期”,一般三期和五期为大期,主要亲戚都要前来,其他“期”为小期,只由主人在家里祭献。“期”过完过“百日”,“百日”过后过“周年”,另外,人死后还要过一次“生日”,谓之“冥寿”。乡人对“冥寿”较为重视,有的甚至制作“冥寿幛”以作留念。韩城市博物馆就藏有冥寿幛两幅。
(14)、三年
对于三年,韩城南北习俗迥异,南原人似关中各县,对三年比较重视,是日,大宴亲邻,排场热闹。而在北原,只不过家祭而已。正如杨茵先生所论,一道魏长城,竟成了韩城保持秦、晋两地风俗的分界线。